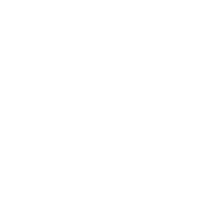六月泪,信仰路
六月,是一个见证了太多欢笑与泪水的时节。它裹挟着阳光下盛放的凤凰花,也夹杂着空气中若有似无的感伤。特别是对于那些刚刚经历完高考的年轻学子来说,它像一场盛大却短暂的狂欢,铺陈着成长的欢愉与阵痛,也拉开了告别的序幕。高考的硝烟散去,有人如释重负地欢呼,更多人是在等待命运的宣判。
另一边,大学的毕业典礼正在上演,镜头定格在青春最明亮的瞬间:一顶顶学士帽抛向空中,像飞翔的梦想在蓝天下划出弧线。可是,庄重的学士服下,藏不住的是不舍的泪水,藏不住的是拥抱背后的沉默与颤抖。毕业生们微笑着说“再见”,却心知肚明可能不再相见。
这一年,毕业生们在各种“最后一次”中反复练习告别。最后一次在教室里并肩而坐,最后一次深夜卧谈,最后一次在食堂抢饭,最后一次随意地说“明天见”。
成长并不总是轰轰烈烈,它常常只是一次又一次默默的道别,一次又一次的失去与放下。
我也曾站在这个六月的路口。高考结束后,在某个充满矛盾和纠结的夜晚,我退出了所有班级群、校友群。没有像别人那样转发感谢母校、感恩老师的文案,也没有参与最后的狂欢。不是我不愿庆祝与感恩,而是我始终觉得,自己没有资格。
我没有考出应有的成绩,也没有成为理想中的自己,如果我去感恩,未免也太过虚伪。看着别人把“逆袭”“圆梦”“全家欢呼”的照片晒到朋友圈,我只想关掉手机。毕业典礼那天,我没有穿上定制班服,没有合照、没有拥抱、没有道别、没有眼泪。拿到毕业证后,在人群还没聚集起来之前,我就溜出了学校。我甚至不确定,是否有人察觉到我的离去。就这样,我从一个充满“和和气气大家庭”氛围中的集体里抽离出来。
回去的路上,想起在学校的那段日子,让我很快意识到:我是个“不像样”的家伙。班级里年纪相仿的同学们,竟然早已练就精明老练的处世能力,拍马屁、玩政治、游刃有余地向组织靠拢、获得各种荣誉和青睐。我观察过他们,有时也能看穿那些“先进”背后的算计,比如先是争先恐后地积极报名献血,然后在献血体检前,特意在宿舍喝了几大杯热水提升血压......所有的一切就像一根无形的鞭子驱动着我们,谁能更早靠拢组织,谁就能获得更多资源。这是默认的游戏规则,而我,却始终不知道该如何参与。我不是不想积极,只是手足无措。
那个夏天,我没有陷入深深的自我否定,但像在六月燥热的空气里溺水一般,连呼吸都显得艰难......
我不是没有退路,只是我的灵魂不能妥协。我究竟是谁?我到底从哪里来,又该何去何从?耳边有声音轻轻地、若有若无地唤我出走。我渴望被拯救,可又有谁能拯救我呢?我迫切想要从这些困住我内心的问题中挣脱出来,于是我鼓起勇气,不惧走入这条看不见的信仰路,揽风而行,星夜兼程。
理解,是为了不再传递伤害
我很幸运,在此后的大学时期找到了自己的信仰,认识了耶稣基督——这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恩典。
带着基督信仰,如今我可以超然地看待这段校园经历,也时常反思自己当初那么做是不是有点“抓马”。人人都有罪,绝大多数人却不自知,也是在扭曲的体系中长大,在不安中生存、在惧怕中前行。他们以为只有苛刻、控制、迎合权威,才能保全自己。于是,他们有意无意地复制伤害,带着被压抑的灵魂,一路老去,却从未醒来。
那些曾施加我痛苦的人,他们不承认自己是受害者,当然也从未意识到自己伤害了谁。而耶稣基督引领我前行,开启我未曾察觉的眼睛,也唤醒了我沉睡已久的心灵。我不必模仿他们的样子:那种居高临下的怜悯,那些为了获得心理满足的施舍;也无需刻意将青春重新包装成美好的谎言。盲目怀旧是没有必要的,想着如何报复他们同样很幼稚。此刻,我唯一能做的,是在理解中终止恶的传递,在信仰中找回纯粹的爱与拯救——为了一个更好的世界,为了未来的孩子们。
人们说的悲剧,其真正根源深植于人与生俱来的罪性和自我中心。确实,世间一切苦难的缔造者,无不源于那膨胀自私的“我”和排他的“我们”。当个体或群体以自我为核心时,一种本能的隔绝便油然而生。这种隔绝,既是自我保护的应激反应,更是一种人为的划界,其深层意图在于将权力紧紧攫取在“我”或“我们”手中。这导致了人际间的疏离,更催生了群体间的对立与纷争,最终导致更大的悲剧。
我此前一切的愤世嫉俗或是玩世不恭,剥开层层外衣,只不过是我微不足道的年少敏感和个人情绪的回音壁,只在我心中回响,并无什么崇高或价值可言。我的存在没有为他人的幸福添一寸光亮,那些自诩为真诚的言语,也许不过是伤人的利刃,徒增他人的不适与疏离。我是否应该沉默闭嘴?是否应该低头认罪?
当我第一次在耶稣面前看到自己时,才真正明白了何为“自我”。回想过去那份良好的自我感觉,如今看来竟是如此荒谬。我曾慨叹人心的丑陋,却从未审视自己内心的阴暗;我曾埋怨周遭环境的黑暗,却从未察觉自己是否曾为这世界增添过一丝光明。社会如同一口酱缸,一度是我不安良心的最大慰藉,让我得以自欺:我本是白色纯洁的,不过是失足跌入酱缸,才沾染了些许酱色罢了。
然而,只有我在耶稣面前坦露一切,才幡然醒悟:我骨子里便是那酱色,因此才能在酱缸中如鱼得水、恣意翻腾。我的生命,不过是一只破旧的皮囊,外面缀着几块虚饰的遮羞布罢了。但当祂的怜悯如潮水涌来,当那赦免的大爱不顾一切地临到我,不是理性战胜了疑问,而是内心彻底降伏了。
其实,每个人的内心都极其渴望爱与扶持,却往往被裹挟进一个充满算计与孤立的大环境中,不断堕落,难以自拔。
耶稣啊,我爱你,我只求你赐我一个全新的心。
上帝所教的爱与盼望
“爱是恒久忍耐,又有恩慈……”寥寥数句,字里行间,就道出爱的真谛,说尽一切不可言说。这是我能背出的第一句上帝的话,也是我第一次读圣书时,就直觉性地被这几段文字安慰。那时的我,不知道爱是什么样子,只是觉得,若真的有这样的爱,那它该是比阳光还温柔的东西。
奇妙的是,在我第一份实习工作中,我遇见了一位叫凯莉的女领导。她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,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,平时身上总带着圣书。她没有多少宏大的言语,也不常说大道理,但她的生命本身,就像一封活出来的书信。她的工位上贴着一张粉红色的贴纸,上面写着“爱是恒久忍耐”。有时她加班太晚,便把孩子的画贴在桌旁,有一张是她儿子用蜡笔画的十字架,涂得歪歪斜斜,却让我鼻头发酸。
在凯莉身边实习的那几个月,我第一次真实地看见了——爱与信仰若能浸润日常,会是怎样温柔又有力量的存在。她从不苛刻下属,不居功、不高高在上;当众人争辩不休时,她总是第一个安静下来,耐心听完每一个人的发言;别人偶尔迟到一次,她不会指责,而是体谅对方通勤的辛苦;即便是一个微小的善意举动,她也总会真诚地表达感谢。
有一次,我忍不住问她:“凯莉老师,你这样从不摆出领导的架子,真的好吗?”
她只是轻轻一笑,说:“当然啦,我在努力践行爱人如己,我们爱别人,乃是因为我们都是祂手中蒙怜悯的器皿。”
那年我离职时,她送我一幅亲手绣的作品——六个字温柔端正地落在素布之上“爱是恒久忍耐”。我一时说不出话来,只觉得心中一角悄然亮了起来,如同某个被遗忘已久的应许被重新拾起。我之所以对凯莉有很深的印象,是因为她有一颗纯净而美好的心,一直以来对我关怀备至,尤其是她总耐心地在空闲时间带我读经、祷告。
保罗说:“如今常存的有信,有望,有爱,这三样,其中最大的是爱。”而如今,我愿带着这份爱与盼望,继续前行。
持爱为光,行远未央
离开那个曾困住我的校园后,我有了新的工作、新的朋友、新的居住环境、新的爱情......
我走出热闹的校友群,走出那个喧哗而拥挤的人生主场,走进了一片更为辽阔的原野。毕业若干年后,我终于找到曾经那个迷茫孤寂的少年,再面对他,我竟羞愧不已,无言以对。
成长不一定来自荣耀,更多时候,它从理解开始,从宽容展开。我们不再需要去报复谁、证明什么,也不再执着于把人生活成一场完美的答卷。那些走错的路、放弃的舞台、被误解的沉默,原来都在信仰中,被悄悄收纳为爱的痕迹。
我无需等待掌声与认同,只要确定那天上的星辰未曾熄灭,只要祂的眼目仍看顾我的脚步,那我就可以一步步地走下去。
我不过是浩瀚宇宙中一粒渺小而软弱的尘土,却终于鼓起全身的勇气,向那位创造天地、海洋与万物的全能主宰敞开了心门,伸出颤抖的求助之手。也正是在这一刻,我结束了多年无知而迷惘的日子,第一次真诚地归回祂面前,认出祂是主,而我是祂所造、所爱的。
我走向的,不再是昔日的荣辱得失,而是那永不止息的爱——在希望中生根,在信仰中结果。因为那位看顾百合花的主,正温柔地牵引着我,陪我走过旷野。
卢梭在《忏悔录》中写道:“我以回忆往事滋养自己,在我体内寻找养料。”是啊,人生终究是一场一场的别离。无论是亲人、朋友、爱人,甚至是那个曾经拼命奔跑、也拼命挣扎的自己。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,我们无法预知哪一次遇见会成永别,所能把握的,也许只是趁当下的每一刻,好好说一句“谢谢”,好好去爱,不留遗憾地活在当下。
此时初夏,花树的香气浓烈而真实。我再一次路过小区旁的校园,望见那些穿着蓝色校服的少年,步履轻快、目光澄澈,恍若昨日的自己。再过些时日,他们将踏入人生的又一扇门,青春像一场晨光乍现的远行。每次告别都包裹着时光的体温,也铭刻着命运中彼此擦肩而过的恩典。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祝福,在各自的旅程中,无惧风雨,不问归期,永远心向爱与光明。
立场声明
CT特约/自由撰稿人文章,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立场,供读者参考,CT保持中立。欢迎个人浏览转载,其他公众平台未经授权,不得转载!
版权声明
凡本网来源标注是“CT”的文章权归CT所有。未经CT授权,任何印刷性书籍刊物、公共网站、电子刊物不得转载或引用本网图文。欢迎个体读者转载或分享于您个人的博客、微博、微信及其他社交媒体,但请务必清楚标明出处、作者与链接地址(URL)。其他公共微博、微信公众号等公共平台如需转载引用,请通过电子邮件(jidushibao@gmail.com)、电话(010-82233254)或微博(http://weibo.com/cnchristiantimes),微信(jidushibao2013)联络我们,得到授权方可转载或做其他使用。